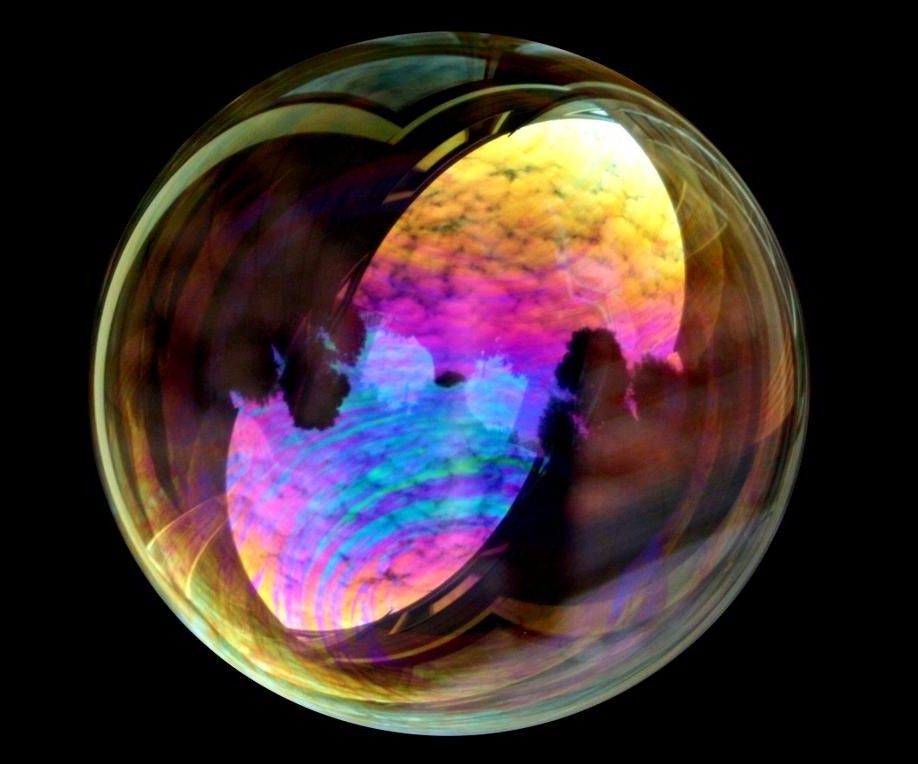
长期以来,量子纠缠现象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的一部分,当量子纠缠现象彼此神秘地相互作用时,无礼地违反了以超光速传播相互作用的禁令。 正在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创建量子计算机的前景。 人们相信,它们的数据元素-量子位将通过量子纠缠机制发生变化并传输其信息状态。 像DARPA这样的务实组织慷慨地资助了这一出色的科学。 同时,有一种严重的观点认为,EPR悖论意义上的量子纠缠是扎根于对量子力学理解的表层的神话。
EPR悖论
爱因斯坦手里拿着一条横幅,对量子力学进行了攻击,上面写着“上帝不玩骰子”。 在1935年发表的著名文章[0]中,所谓的 EPR悖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 从这个实际上是诡辩的悖论中,量子纠缠的神话诞生了。
根据其作者的一篇文章,EPR的主要思想如下。 假设有一对量子对象1和2,形成具有波动函数的单个系统
Psi(x1,x2) 变量集在哪里
x1 和
x2 分别用于描述子系统1和2的行为。 如果指定了全套
u1(x1),u2(x1), ldots,un(x1), ldots 对于系统1的某些可观察物的本征波函数,则该函数
Psi(x1,x2) 在傅立叶级数中分解:
Psi(x1,x2)= sum inftyn=1 varphin(x2)un(x1)
现在假设子系统彼此远离,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相互影响。 如果然后我们测量系统1的(可交换的)可观测值,那么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它将跳到本征态
uk(x1) 。 在令人困惑的范例中,此事件具有戏剧性的名称“波动函数崩溃”。 因此,EPR的作者进一步认为,整个系统作为整体具有波动函数进入状态
varphik(x2)uk(x1) 。 这意味着子系统2突然能够
varphik(x2) ,尽管子系统1和测量仪器对此没有影响。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主要的影响,它与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思想相关,即远处的量子对象1和2的无法理解和无法解释的瞬时相互作用。它的存在在于,在测量与系统1相关的某些物理量时,会自动且立即系统状态2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推理,一次有两个错误。 首先是波函数
varphik(x2)uk(x1) 一般而言,它不对应于统一系统的自身状态。 因此,不需要后者
varphik(x2)uk(x1) 在仅与系统1相关的测量过程中突然发生变化。然而,仍然出现问题:测量1之后,子系统2处于什么状态? 答案很简单而且显而易见-她的状况不会改变。 实际上,由于对象1和2在所考虑的情况下是独立的,因此
Psi(x1,x2)= Psi1(x1) Psi2(x2)= Psi2(x2) sum inftyn=1cnun(x1)= sum inftyn=1cnun(x1) Psi2(x2)
在哪里
Psij(xj) -系统的波动功能
j=1,2 分开考虑。 因此,只要子系统1处于自己的状态
uk(x1) ,子系统2自动处于...其原始状态
Psi2(x2) 。 这是可以预期的!
第二个错误是,一对非相互作用的对象1和2正式组合成一个系统,实际上在测量中没有受到干扰,而这仅与子系统1有关。这种“干扰”无法使组合的系统跳入一个子系统中。本征态(通过组合集合1和2获得的一组完整的通勤可观察物)。 为此,有必要激怒整个系统,即也确实对对象2起作用。
因此,EPR的伪悖论仅迫使我们阐明扰动的概念。 但是相反,它们给了它绝对的和形式上的含义,就好像蝴蝶的翅膀拍打被认为是对宇宙的干扰……尽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上面问题的确切答案是子系统2在测量1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EPR的作者从他们的伪悖论中得出了关于量子力学不完备性的深远结论。 该理论需要额外的参数来描述量子系统。 排除任何不确定性并使其行为具有古典精神确定性的参数。 从爱因斯坦的角度来看,科学根本还不知道这些隐藏的参数及其行为规律,因此受到量子预测概率性质的限制。
在对一对粒子的量子纠缠效应的流行解释中,EPR的自由阐述之后,它们总是指守恒定律。 考虑一对电子的情况。 尽管经常举一个带有动量的“纠缠”电子对的例子,但讨论动量守恒毫无意义。
pm vecp 。 由于动量算子具有连续的频谱,因此很难实现其本征态。 因此,在量子水平上,考虑具有矩量的一对电子是毫无意义的。
pm vecp 。 因此,我们撇开了动量,并考虑了一个“纠缠”电子对的情况,该电子对在Z轴上的自旋总投影为零(单个)。
保持旋转的投影意味着对操作员而言
mz 自旋在z轴上的投影发生
[mz,H]=0 在哪里
H 是该系统的能源运营商。 特别是,这意味着如果系统最初处于操作员自己的状态
mz ,那么将来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
t 处于可观察的状态
mz ,尽管状态向量可能会随时间变化。
对于单个电子,算子
mz 有两个特征向量
|1 rangle 和
2 rangle 这样
mz(|1 rangle)= frac12 frach2 pi|1 rangle qquadmz(|2 rangle)=− frac12 frach2 pi|2 rangle
假设一对电子最初处于状态
c cdot(|1,2 rangle−|2,1 rangle) 在哪里
c -任何复数。 这是向量
|a,b rangle 对应于一对电子的状态,即第一电子处于
|一个 rangle 第二个能够
|b rangle 。 条件
c cdot(|1,2 rangle−|2,1 rangle) 背面专有
Mz 由两个电子组成的系统,因此在测量时,系统将保持该状态并获得零值
M′z=0 对的后面。
在电子沿不同方向散射的过程中,如果系统在第一次测量之前保持隔离状态,则单重态的自旋态将不会改变。 这意味着对于每个
t 一对电子处于一种状态
c(t) cdot(|1,2 rangle−||2,1 rangle) 这对操作员来说是合适的
Mz 并符合自己的意思
M′z=0 。 根据关于一对纠缠电子的流行论证,当测量一个粒子的自旋时,系统将跳到算子的本征态
Mz 。 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由于系统已经处于其自身状态(一整套通勤可观测物,包括
Mz ,她将在测量后保留在其中。 因此,只有向量前面的数值因子会改变
|1,2 rangle−||2,1 rangle 。
因此,被测电子向态的跃迁
|1 rangle ,第二个陈述
|2 rangle 不会发生。 一个矛盾是,被测电子仍然会进入其算子的本征态
mz 。 因此,当测量电子之一的自旋时,单线态的结合态将被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电子的状态将保持不变,即在自旋方面不确定,即
|1 rangle+|2 rangle 。
在令人困惑的范式中,还考虑了一对处于相同偏振态的光子,因此该对的一般状态可以由矢量指定
c(|1,1 rangle+|2,2 rangle) 在哪里
|1 rangle 和
|2 rangle 在垂直方向上设置偏振态。 如果在测量其中一个光子时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1 rangle ,那么据推测这将需要将配对转换为状态
|1,1 rangle 即第二个光子瞬时跳到相同的偏振态
|1 rangle 。 但是,类似于电子单重态的示例,可以认为一对光子将保持其自身状态
c(|1,1 rangle+|2,2 rangle) 。 这种矛盾意味着对两个光子之一的测量会破坏系统,此后第二个光子仍保持其原始状态
|1 rangle+|2 rangle 。 在这里也不会出现EPR方面的纠缠。
不平等贝拉
1964年,约翰·斯图尔特·贝尔(John Stuart Bell)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1],其中他对隐藏参数假设进行了严格的分析。 贝尔的这些令人惊讶的简单论点对从20世纪末到现在的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推理过程中,贝尔推导了不平等
1+P( vecb, vecc) geq|P( veca, vecb)−P( veca, vecc)| 在哪里
veca, vecb, vecc -这些是空间中各个方向的单位矢量,在两个方向上散射的两个粒子(电子)的自旋投影到其上。 最初,粒子的总自旋为零,即 形成单线态。 同时
P( veca, vecb) 表示一对随机变量的不规则相关系数
vec sigma1 cdot veca 和
vec sigma2 cdot vecb 是自旋变量的投影
vec sigma1 和
vec sigma2 向量方向上的粒子1和2
veca 和
vecb 相应地。 换句话说
P( veca, vecb) 是数字乘积的平均值
vec sigma1 cdot veca 和
vec sigma2 cdot vecb 。 注意,这些具有价值
\下午1 。 如果关于隐藏参数的爱因斯坦假设是正确的,则该不等式成立。
lambda 量子系统。 并且可以进行统计检查。 将来,类似地获得其他不等式,这些不等式不仅适用于单线态电子对,而且所有这些不等式都称为贝尔不等式。 例如,这:
|P( veca, vecb)+P( veca, vecb′)+P( veca′, vecb)−P( veca′, vecb′)| leq2
仅在存在隐藏参数的情况下也有效
lambda 决定其行为的量子系统。 此外,由于这些参数的行为规律未知,因此将它们视为随机变量。
为了说明最后一个陈述,请考虑扔硬币的经验。 显然,废弃硬币的飞行由许多数量决定,这些数量描述了硬币的形状,质量分布,投掷的详细条件,跌落表面的形状以及确定问题答案的其他因素:“正面还是反面”。 充分考虑所有这些“隐藏参数”,贝尔用符号表示
lambda ,那么您可以对硬币的下落方式进行100%可靠的预测。 但是,这种会计处理太复杂了,这不是很必要,因此,它们满足于硬币如何下落的概率预测。 因此,隐藏参数应视为随机变量。 问题:类似的隐藏参数是否存在于任何量子系统中,或者没有这样的参数,并且亚原子物体的随机行为是事物本质所固有的吗?
在实验中所谓 纠缠在一起的粒子(通常是光子),所需的结果始终违反了贝尔的不等式。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际上已经观察到了这种违反,今天习惯上将它们解释为纠缠的量子态出现的证据。 同时,实验人员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目的是将记录粒子自旋或光子极化方向的设备传播到最大可能的距离,以排除物体和测量仪器的相互影响。 从而使相互作用的瞬时传输的效果尽可能令人信服,这形成了量子隐形传送幻想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违反贝尔不等式意味着两件事之一。
a)量子系统没有隐藏参数。 这与量子力学完全一致,与纠缠无关。
b)存在隐藏参数,然后其中一个子系统的测量会影响另一个。 因此,量子纠缠是存在的地方。
因此,没有理由争辩说违反Bell不等式的实验证明了EPR纠缠现象。 合理地假设它们包含a),即,量子力学不需要隐藏的参数,并且不需要提升Bohm的精神。 但是,这些违反被认为是EPR的证据-光子对纠缠。
这种范例是在Aspe和其他建立类似实验的科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 除了毫无疑问地违反了贝尔不等式外,据称还观察到了相互遥远的光子的偏振方向之间的相关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贝尔的不等式来实验性地测试EPR。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文章[1]的判断,Aspe本人仅将相关性视为纠缠的证据。 但实际上,每个落入光电倍增管的光子都有一个“相关性”。 更准确地说:他几乎同时达到了两个光电倍增管(见下文)。
阿斯佩经验
杰出的实验者和量子魔术经典人物Alan Aspe(Aspect)的经历,为EPR的神话-教条的转化做出了主要贡献。 Aspe等人的实验结果是根据光子作为点粒子的概念来解释的(通常对波粒对偶性有所保留)。 这是错误的,因为 光子没有薛定ding表示[2]。 简而言之,对于这些粒子,空间坐标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不能说在某个时间点光子在某个地方。 它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小波包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化失去了意义。
在这方面,引用Dirac是合适的(PAM Dirac,第25 [2]页)。
“ ...
假设有一束由大量光子组成的光束分成两个强度相同的分量。假设光束强度与可能的光子数量有关,我们将得到总数的一半落入每个分量中如果这两个分量进一步干涉,那么我们必须要求来自一个分量的光子可以干扰另一个分量的光子,有时这两个光子会被破坏,有时会变成四个 这是与能量守恒定律相违背的,将波函数与一个光子的概率联系起来的新理论克服了这一难题,因为每个光子都部分地位于两个分量的每一个中,然后每个光子仅自身干涉。永远不会发生两个不同的光子 。“
海森堡的一句话中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与EPR悖论有关,并且与对阿斯佩实验的解释有关(W. Heisenberg,第34 [3]页)。
“
考虑到这些考虑因素,这里应该指出一个由爱因斯坦提出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个光量子,它由麦克斯韦波构成的波包表示,因此,给它分配了一个已知的空间区域,并且在不确定性关系的意义上,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通过半透明板的反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波包分解为两部分:反射和透射。 在波包的一个或另一部分中找到光量子的可能性。足够长的时间后,这两个部分将被任意地彼此远离。如果现在根据经验确定光量子位于波包的反射部分中那么它会同时给出在另一部分中找到光量子的概率等于0。在数据包反射的一半的位置处的经验从而在任意距离处产生某种动作(波包的减小!)。 另一半在哪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动作以超光速传播 。
因此,尝试使用干涉仪检测EPR纠缠的光子对是没有意义的。 假设我们用半透明镜分割光束,然后使一个光束通过偏光镜。 根据EPR范式,出现了来自两个光束的成对的相同偏振光子的纠缠对。 这可以通过干涉来验证,但是由于每个光子都会干涉自身,因此在不同位置测得的偏振的重合不能解释为EPR纠缠。
隐含假定的点光子极化的可能性构成了错误解释Aspe实验的基础。 我们首先对这些实验进行简要说明(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1])。
使用级联荧光源,其中原子以一定间隔发射成对的量子 Ť ≈ 5纳秒。在第一个实验中,该对光子中的一个光子的波长为551.3 nm(绿光),另一个光子的波长为422.7 nm(紫色)。根据动量和角动量的守恒定律,我们相信在每个级联中,光子沿不同方向散射,具有相同的圆偏振方向-左右概率为0.5,这等效于在X和Y轴方向上停留在两个线性偏振态的叠加上。 Aspe和他的追随者相信,这对光量子是在纠缠的偏振状态下产生的:| Ψ ⟩ = 1√2(|R1⟩⊗|R2⟩+|L1⟩⊗|L2⟩)=1√2(|x⟩⊗|x⟩+|y⟩⊗|y⟩)
|R1⟩=|L2⟩=1√2(|x⟩+i|y⟩),| 大号1 ⟩ = | [R 2 ⟩ = 1√2(|X⟩-我|ÿ⟩)
州 | X - [R 一Ñ 克升ë ,
| ÿ ⟩沿偏振轴的方向相遇时,条件| [R Ĵ ⟩ ,
| 升Ĵ ⟩光子数的圆极化的两个方向-Ĵ = 1 ,2 。
EPR-纠缠是指,如果检测到一个光子沿X轴极化(为此足以使它通过X-取向的偏振器),则第二个光子将在同一瞬间自动处于相同状态(可以使用第二个光子进行检测)偏光片)。对于Y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的是可以测量的一对纠缠光子的偏振方向之间的相关性。Aspe实验方案在该方案中,一对激光器激发级联辐射的荧光源,根据Aspe的说法,该源发射成对的纠缠光子。它们每个都通过自己的偏振器(Pol I和Pol II),然后通过频率滤波器进入光电倍增管(PM I和PM II)。后者本质上是单个光子的检测器,并根据引发光电效应的电子雪崩原理工作。光电倍增管控制电路的组织方式是,在大约20 ns的时间窗口内检测每对量子。来自两个不同原子的随机光子对不可能进入其中。因此,电路几乎可以肯定只能将一个发射级的发射对固定。这平均每秒发生100次。回想一下,每个这样的对都被认为是EPR-感到困惑。如果现在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计算了其中一个偏振器(“左”或“右”)被移除的情况下的对数,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给定方向上左光子的偏振事件之间的相关系数 → a,然后向右转→ b 。
这样的测量可以验证贝尔的不等式,还可以揭示每对光子的极化之间的相关性(针对不同的方向 → 一个 和
→ b )
那是Aspe小组所做的。但是,在Aspe实验中,可能会有单个光子以具有球形前部(波表面)的波的形式到达两个光电倍增管。根据量子电动力学[4],具有给定角动量的光子场以这种波的形式精确地传播。可以证明,由于离发射器的距离不同,该波以相同的相位到达两个偏振器的每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场强矢量之间的角度对于任何波表面, E和每个偏振器的轴都是相同的。因此,一个光子波与两个偏振器均等地相互作用。这会产生一对纠缠在极化中的粒子的错觉。可以说,光子计数器平均通过两次被触发≈ 5纳秒,因为它应该是在辐射级联。但是,光电倍增管的响应时间是基本估算的〜10纳秒。在此期间只能捕获一个光子。实际上,它是一个以球体为中心的波包| r | = Ç 吨 。
如果包装尺寸 Δ - [R 〜1米,这对应于多普勒加宽谱线〜10 - 3 ∘ 甲,同时穿过光电倍增具有一个阶段的光子之间的顺序间隔。在Aspe实验的条件下,这种扩展是可能的。因此,在第一个光子上触发一对光电倍增器之前,无法检测到第二个光子,并且当两个设备都准备好接收第二个光子时,它的数据包已经通过。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对光电倍增器仅捕获每个级联的两个光子中的一个。我们还注意到,在所考虑的状态下,光子的运动方向未定义。这是由于以下事实:冲动及其动量没有减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用经典力学的类比作为一对光子纠缠态的原因是不合适的。另外,光子发射伴随着干扰。在此之后,原子将不会处于零矩状态,而会处于矩本征态的叠加状态。因此,守恒定律并不意味着一个级联形式的一对光子的状态| Ψ ⟩ = 1√2(|- [R1⟩⊗|- [R2⟩+|大号1⟩⊗|大号2⟩)=1√2(|X⟩⊗|X⟩+|ÿ⟩⊗|ÿ⟩)
在辐射期间,该对光子之间的距离为 〜1 m。这样的夫妻天生就是个想法,这与常识相反。 但是,后者适用于所有量子魔术。
因此,Aspe实验的结果具有与EPR纠缠无关的解释。 需要更准确的估计,但是已经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实验中没有观察到任何联合的,EPR纠缠的状态。 显然,所有的实验都与所谓的 纠缠的光子。
可以追溯到EPR悖论的相距很远的粒子的纠缠态的概念已经广泛普及,并且已经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一部分。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证明它没有基础。 图中的肥皂泡象征着具有给定角动量的光子的波前,以及基于EPR纠缠的量子计算机理论。
参考文献0.爱因斯坦(Einstein A.),波多尔斯基(Podolsky B.),罗森(Rosen)N.,可以认为物理现实的量子力学描述是完整的,
1. A.方面。 贝尔定理:实验学家的幼稚观点,在量子[联合国]言语-从贝尔到量子信息,2002年,RA Bertlmann和A. Zeilinger,Springer。
2.下午 狄拉克。 量子力学原理,1960年,莫斯科:Fizmatgiz(PAM Dirac英文版的翻译。量子力学原理,1958年,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32年)。
3. V.海森堡。 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莫斯科:GTTI(W。Heisenberg的德语版翻译:Physikalischen Prinzipien der Quantentheorie出版社,1930年,莱比锡)。
4. V. B. Berestetskiy,E.M。 Lifshits,L.P. 皮塔耶夫斯基。 量子电动力学,莫斯科:科学,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