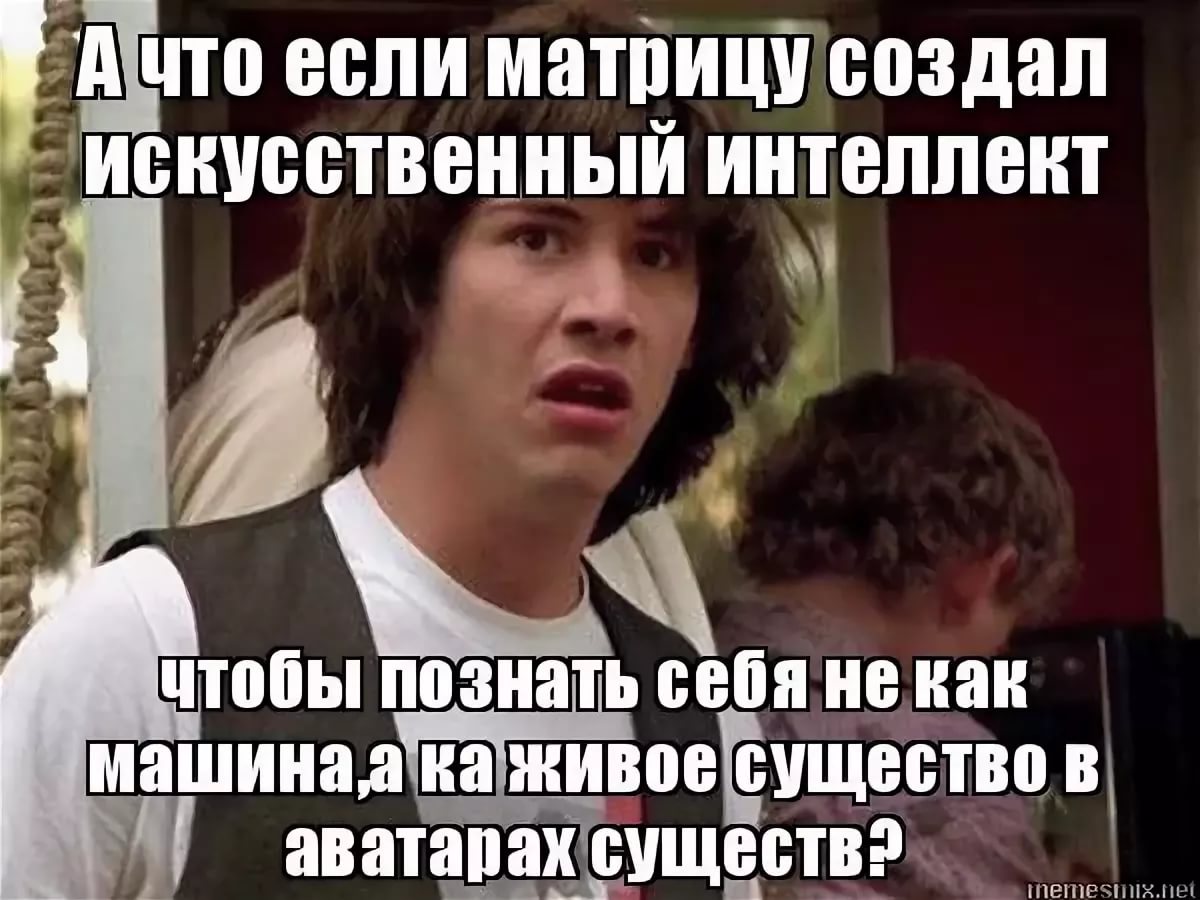如果对于某些人来说,人工智能的未来似乎是严峻的反乌托邦或为生存而斗争,也许他们应该理清他们关于权力和屈服本质的想法。
剑桥大学勒沃胡姆大学未来智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卡文(Stephen Cave)这样说。 在他的论文中,他建议探索知识优势的历史-放弃这个错误的概念。
对人工智能概念的迷恋主导了20世纪下半叶的进步世界。
他们考虑了心理能力,进行了讨论,并开发了测量心理能力的新方法。 欧洲领先国家的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和求职者已经通过(并且正在接受)智商测试。
即使在那时,可以通过血压或脚的大小来衡量智力的想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我们认为,智力水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地位,这是更古老的想法。
这种理解贯穿于西方思想的整个历史,从柏拉图哲学到现代政治家的信仰。
智力是政治
纵观历史,西方世界一直在智力方面决定一个人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 例如,我们传统上(针对大多数人口)将高水平的心理能力归功于
该国的医生,工程师和高级
官员 。
我们认为,智力水平使我们有权控制其他人的命运:我们殖民,奴役,剥夺了生殖器并摧毁了那些我们认为不那么聪明和发达的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对情报的态度开始迅速改变。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领域的重大进展,并且似乎正处于巨大的科学突破的边缘。 从关于人工智能的复杂知识和笑话的数量来看,我们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同时又非常害怕。 为了理解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感到如此恐惧,以及为什么我们对心理能力这个话题如此漠不关心,有必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它,并追溯哲学思想如何将智力变成证明无休止的征服的工具。

刻板印象的历史线索
柏拉图使思想成为强大者的必要关于思维的第一个话题开始争论柏拉图。 在他的著作中,他认为反思过程具有特殊的价值,认为无意义的生活不值一分钱。 值得记住的是,柏拉图生活在一个神话和神秘意识构成人类心灵自然环境的世界中。 因此,他当时认为可以通过思维了解世界的说法是非常大胆而诱人的。
柏拉图在他的作品《国家》中宣布只有哲学家才能统治国家,因为只有他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理解,柏拉图催生了知识精英的理念-只有最聪明的人才可以控制他人。
当时的想法是革命性的:是的,雅典已经尝试将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 但是对统治者的要求非常模糊:成为一名男性公民就足够了–毫无疑问的是智力水平。 在其他地区,政府席位的分配是通过贵族的成员身份(贵族制),或者是通过上帝的天意任命(神权统治),或者仅仅是通过实力水平(暴政)来分配。
 壁画是“雅典学校”,描绘了列奥纳多和布拉曼特以及毕达哥拉斯和亚里斯多德。
壁画是“雅典学校”,描绘了列奥纳多和布拉曼特以及毕达哥拉斯和亚里斯多德。亚里士多德想出了男人的力量
柏拉图的创新思想成功地落在了那个时代伟大思想者的沃土上,他的门徒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他在更实际和系统的世界观上与老师有所不同,因此他使用“灵魂的理性要素”来创建自然社会等级制的概念。 他在《政治》中指出:
“毕竟,统治和服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而且从诞生之日起,有些生物就(应该认为其中的某些)应服从,而另一些则要进行支配。
基于此,受过教育的男人很自然地统治着女性,体力劳动者和奴隶。 在此层次结构的下面,只有没有理由的动物,它们只需要有人来控制它们即可。
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如何从柏拉图式的理性要素至上观念转变为亚里士多德式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预设了思考人的完全自然的力量。这列思想上的不公正现象仍然以燃料为燃料,这是由2000年前两名大胡子男人所为。 现代澳大利亚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声称,希腊哲学的两个巨人,带着一系列可疑的二元论,仍然设法影响我们关于思想的观念。
对于我们通过最聪明的人的权利将主导关系视为完全自然的事实,我们应该感谢亚里斯多德。

笛卡尔为毁灭地球奠定了道德基础
伟大的二元论者里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作品使西方哲学达到了顶峰。
如果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至少承认动物至少有一些基本和原始的权利,但仍属于精神活动,那么笛卡尔(笛卡尔)便完全否认了他们的这项权利。 他认为,意识是人的唯一优势。
笛卡尔的哲学反映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千年历史:它赋予了心灵灵魂的所有权,一种神圣的火花,仅继承给那些以上帝的形像和形像所创造的幸运者。
康德的正当殖民政策
心灵定义一个人的观念已经通过了启蒙运动。 也许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的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道德意愿仅对以下思想存在:“人”和“自身之物”。 在他看来,没有思想的生物“只有相对价值作为手段,因此被称为事物”。 有了他们,您可以做我们所希望的。
康德认为,理性的人具有尊严,而一个无理,无思想的生物则无能为力。这些推论后来成为殖民政策的基石。
逻辑是这样的:不是白人不那么聪明。 他们无法独立控制自己和自己的领土。 这不仅是合理的一步,而且是任何白人进入其国家并破坏其文化的道德义务。
同样的逻辑结构对于被认为过于轻浮和脆弱以至于无法分享理性人的特权的女性而言,效果最佳。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心理学计量学,测量心智的伪科学之父,也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 受物种起源的启发,高尔顿(Galton)提出了一种观念,即智力是可以继承的,可以通过选择来提高。
高尔顿不仅仅局限于理论计算: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超过20,000名妇女因高尔顿测试结果差而被绝育

那么,为什么我们害怕智能机器人呢?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工智能出现的可能性使我们感到恐惧? 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聪明人总是占主导地位的事实,而我们绝对不希望站在路障的另一端吗?
作家和导演长期以来一直在猜测机器起义的主题。
如果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最聪明的皮肤被剥夺了,而另一个发达国家可以在另一个国家殖民,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惧怕超智能机器的奴役。 人工智能对我们构成了生存威胁 。
对我们来说,这是给白人欧洲男人的。 数十亿其他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服从,直到今天,许多人仍在与侵略者作斗争,因此对他们而言,人工智能对奴役的威胁仍然是一个绝妙的故事。
白人欧洲人习惯于以拥有权居于首位,以至于我们中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都带有令人震惊的(非理性的)恐怖。
我并不是说对强大的人工智能出现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 确实存在威胁,但它们与机器人对人类文明的殖民化没有任何关系。
与其考虑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不如考虑我们如何处理自己。
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损害我们,它几乎肯定会发生,这不是因为AI征服人类的愿望,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这会犯错。 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自然的愚蠢。
如果社会坚信最聪明的人-不是获得权力的人,而是寻求解决冲突的人-我们会比我们更害怕智能机器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