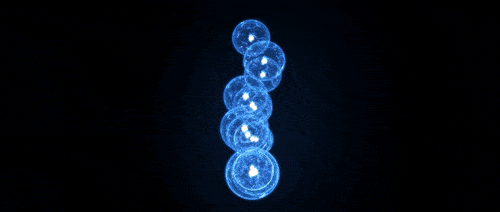
三年前,
洛桑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
Marina Vyazovskaya发现了在8维和24维空间中包装相同尺寸球体的最密集方式(在第二种情况下,在四位合著者的帮助下),使数学家感到惊讶。 现在,他们和合著者
已经证明了更令人惊讶的事情:解决上述尺寸中密集堆积球体问题的配置还解决了与试图避免彼此的点的最佳排列有关的无数其他问题。
例如,点可以表示无限的电子集合,它们互相排斥并且试图以最低的能量稳定在构型中。 或者,这些点可能指示溶液中较长的扭曲聚合物的中心,试图使其自身排列以便不与邻居碰撞。 此类问题有很多选择,而且每个解决方案都具有相同的解决方案并不明显。 数学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由8维和24维组成的空间包含特殊的,非常对称的点配置,众所周知,这些点同时解决了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 用数学语言来说,这两种配置被称为“通用最优”。
这项新的大规模发现认真总结了Vyazovskaya及其同事的先前工作。 匹兹堡大学的数学家
托马斯·海尔斯 (
Thomas Hales)说:“烟花并没有停止。”
他在1998年
证明 ,众所周知的橘子金字塔形排列是在三维空间中填充球体的最密集方式。
8和24将一维连接到一小部分包含通用最佳配置的维中。 在二维平面上,有一个普遍最优的候选对象-等边三角形的网格-但没有证据。 在三维世界中,一个完整的动物园统治着整个世界:不同点的配置在不同情况下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并且对于某些问题,数学家甚至没有关于最佳配置的可容忍的猜测。
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的数学家
理查德·施瓦茨说:“改变度量或稍微改变任务,情况就变得不可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数学世界如此安排。”
要证明普遍的最优性比解决填充球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特别是,由于全局最优性一次包含了无数个不同的任务,还因为这些任务本身更加复杂。 在球体的堆积中,每个球体仅与其最近的邻居有关,但是在诸如电子分布之类的问题中,每个电子都与所有其他电子相互作用,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无关。 “即使从我的早期工作来看,我也没想到可以做到这一普遍最优的证明,”海尔斯说。
纽约大学的数学家
西尔维亚·瑟法蒂 (
Sylvia Serfati)说:“这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这件事与19世纪的重大数学突破相提并论。”
魔术证书
维度8和24的行为与维度7、18或25的行为似乎有所不同,这似乎很奇怪。但是,数学家早就知道,空间中物体的密集堆积在不同维度上的作用不同。 例如,考虑一个多维球体,它被简单地定义为距离中心固定距离的一组点。 如果我们将球体的体积与描述球体的最小立方体的体积进行比较,则尺寸越大,立方体占据球体的空间就越小。 如果您想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盒子中邮寄一个8维足球,那么该球将占用不到盒子体积的2%,而其他所有东西都将是杂散的空白空间。
在每个大于3的维度中,都可以创建类似于橘子金字塔的配置,并且随着维度的增加,球体之间的间隙会增大。 达到第八维后,我们突然遇到一个事实,在这些空间中有足够的空间挤压球体。 结果是形成了极为对称的配置,称为
E 8格栅。 在第24维中,当可以将其他球体塞到间隙中时,会以类似的方式产生
Lich晶格 ,从而创建了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填充球体构造。
由于数学家尚未完全理解的原因,从数论和数学分析到数学物理学,这两个晶格突然出现在一个数学领域或另一个领域。 该著作的五位作者之一,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微软研究院新英格兰研究所的亨利·科恩说:“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原因。”
十多年来,数学家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数值证据,证明E
8和Lich晶格在尺寸上普遍处于最佳状态-但直到最近,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一点。 然后在2016年,Vyazovskaya迈出了第一步,证明了这两个格子是填充球体的最佳方法。
而且,如果针对三维案例的Hales证明长达数百页,并且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昂贵的计算,则Vyazovskaya的E
8案例证明适用于23页。 她的论点的实质与“魔术”函数(数学家现在称之为)的定义有关,该函数给出了Hales所谓的E
8的“证明”,以求最佳球体的填充-难以获得该证明,但在其出现后立即具有说服力。 例如,如果有人问您是否存在一个实数x,使得多项式x 2-6x + 9变为负数,您可以考虑答案。 但是,意识到此多项式等于(x-3)
2 ,您将立即理解答案为“否”,因为实数的平方不能为负。
事实证明,寻找Vyazovskaya的魔术功能的方法非常强大-而且几乎太强大了。 堆积球的任务仅涉及附近点的相互作用,但是Vyazovskaya方法似乎适用于远距离相互作用,就像远程电子一样。
更高尺寸的不确定性
为了证明空间中的点的配置是普遍最优的,首先必须确定这种普遍性。 没有针对任何目的的最佳点配置:例如,当吸引力作用在这些点上时,具有最低能量的配置不是点阵,而是所有点都集中在一个位置的巨大堆。
Vyazovskaya,Cohn及其同事将研究范围限制在排斥力的普遍性上。 更具体地说,他们考虑了单调力,即当点彼此接近时排斥力变强的力。 这个庞大的家庭包括物质世界的许多共同力量。 这包括宇宙的幂定律-包括带电粒子的库仑定律,以及基于钟形的高斯函数,描述了具有许多独立排斥部分(例如长聚合物)的实体的行为。 填充球的任务位于该宇宙的外边缘:球不相交的要求会在其中心之间的距离小于其直径时变成无限强的排斥力。
对于这些单调的力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对于无限数量的粒子,具有最低能量的配置(“基态”)将是什么? 2006年,Kon和Kumar
开发了一种方法,该方法通过比较描述能量的函数和具有非常方便属性的较小“辅助”函数,
从而找到基态的较小能量边界。 他们为每个维度找到了无限的辅助功能,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佳的辅助功能。
 新作品的五位作者:亨利·科恩,阿布金纳夫·库马尔,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娅,斯蒂芬·米勒和达尼洛·拉琴科
新作品的五位作者:亨利·科恩,阿布金纳夫·库马尔,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娅,斯蒂芬·米勒和达尼洛·拉琴科在大多数测量中,Kohn和Kumar发现的数值限制并不类似于最佳配置的能量。 但是在维度8和24中,对于Kon和Kumar检验其方法的每个排斥力,边界非常接近能量E
8和Lich晶格。 很自然地考虑,对于任何排斥力,是否存在某种理想的辅助函数,该函数将使边界与能量E
8或Lich晶格完全一致。 对于填充球的任务,这恰恰是维亚佐夫斯卡娅三年前所做的:她发现了理想的“魔术”辅助函数,研究了一类称为
模块化函数的函数 ,其几个世纪前的特殊对称性使其成为研究的对象。
当涉及排斥点的其他问题(例如电子问题)时,研究人员知道任何魔术函数应满足的特性:在某些点上,它应具有特殊值,并且其
傅立叶变换 (用于测量函数的固有频率)应采用其他点的特殊值。 他们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功能。
通常,构造一个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点完成所需功能的功能非常简单,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同时控制该功能及其傅立叶图像非常困难。 “当您开始做某事时,其中一项就会与您的欲望完全不同,”科恩说。
实际上,这种挑剔无非是伪装成物理学中不确定性的原理。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说,您对粒子的位置了解得越多,对其动量的了解就越少,反之亦然,这是该一般原理的特例,因为粒子的动量波是其位置波的傅立叶变换。
对于尺寸为8或24的排斥力,Vyazovskaya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车队希望对其魔术功能及其傅里叶图像施加的限制恰好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她怀疑如果添加更多限制,将不会有这种功能。 如果减少限制,那么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功能。 她建议,在团队感兴趣的情况下,应该恰好有一个合适的职能。
“我认为这是Marina的一大特色,” Cohn说。 “她很有见识,也很勇敢。”
当时,康恩对此表示怀疑-维亚佐夫斯卡亚(Vyazovskaya)的直觉似乎太过真实了-但车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不仅表明,对于每一种排斥力,只有一个神奇的功能,而且给出了制造方法。 与填充球一样,这种设计立即为E
8和Lich晶格提供了最佳性证书。 施瓦茨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果。”
三角网格
除了解决全局最优性问题外,新的证据还回答了自Vyazovskaya三年前解决堆积球问题以来数学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它的神奇功能从何而来? “我认为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维亚佐夫斯卡娅说。 “他们问:这有什么意义?”
在一项新工作中,Vyazovskaya和她的同事们证明了填充球的魔术功能是模块化形式的一系列构建模块中的第一个,可用于为每个排斥力创建魔术功能。 Vyazovskaya说:“现在她有很多兄弟姐妹。”
对于Kon来说,照片表现得如此出色似乎仍然很棒。 他说:“在数学中,必须通过毅力和蛮力来实现某些目标。” “有时候,就像现在一样,数学似乎要发生一些事情。”
下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对这些方法进行修改,以证明仅剩下的候选对象的普遍最优性:二维平面上等边三角形的晶格。 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数学家
爱德华•萨夫 (
Edward Saff)说,对于数学家来说,没有人能够在如此简单的条件下提供证据这一事实被认为“对整个社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耻辱”。
与E
8和Leach晶格不同,二维三角形晶格出现在自然界的不同位置,从细胞结构到超导体中漏斗的位置。 基于大量的实验和模拟,物理学家已经暗示了这种晶格在各种情况下的最优性。 但是,科恩说,没有人对为什么三角形晶格应该普遍地最佳化有一个概念上的解释,希望这可以提供数学上的证明。
维度2是唯一的维度,但8和24除外,其中Kohn和Kumar的数字下界很好。 这清楚地表明魔术函数必须存在于二维中。 但是,构造魔术函数的命令方法几乎不能转移到这个新领域: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表示E
8中的点与巫妖晶格之间的距离的数字表现得特别好,而这在二维上不会发生。 到目前为止,这一方面“似乎超出了人的能力,”科恩说。
迄今为止,数学家正在庆祝他们与8维和24维空间的奇异世界相关的新见解。 正如施瓦茨所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可能看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